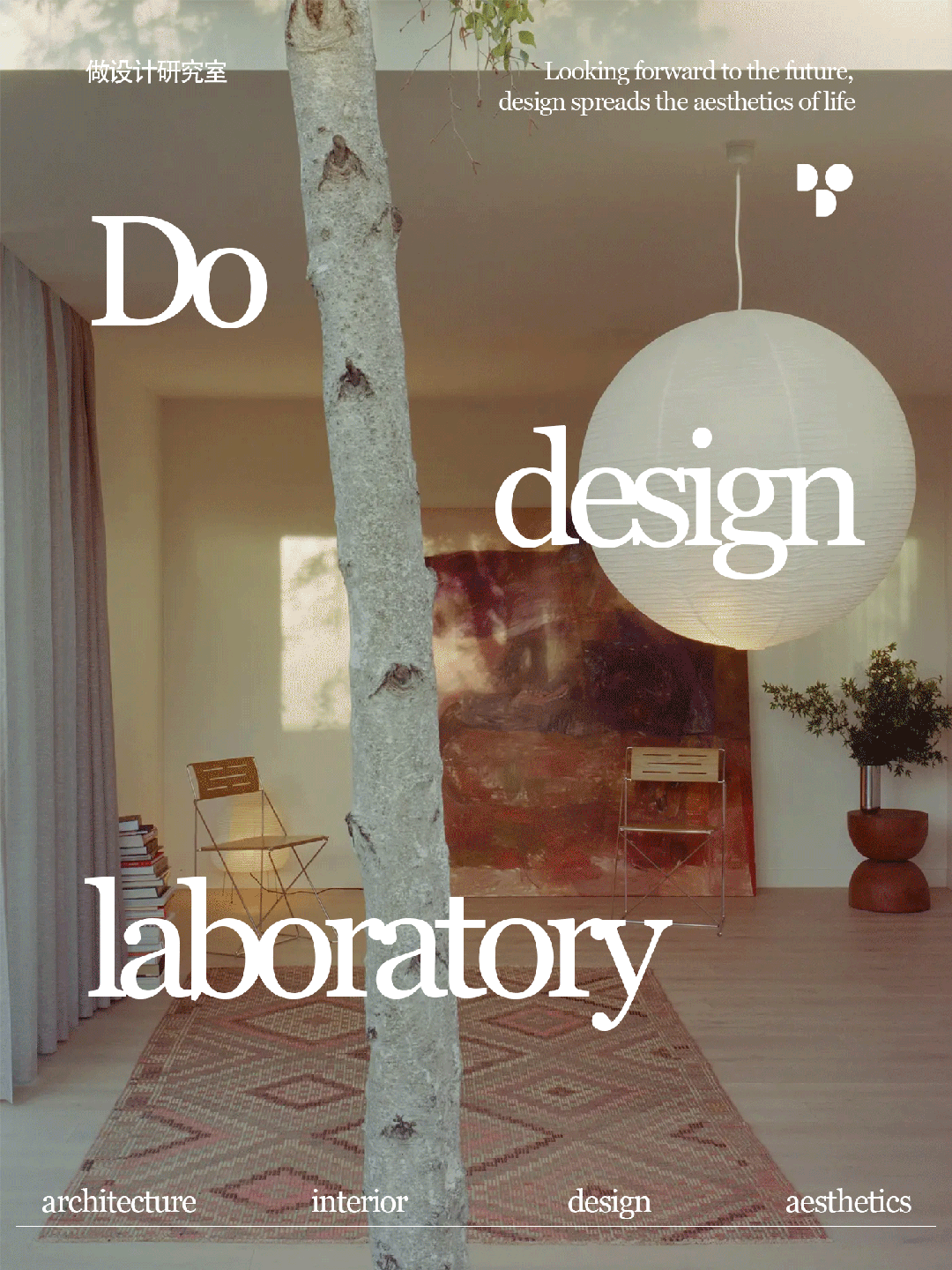新作|青天制作所 :百花书局,微型剧场的“拆”与“合” 首
2025-08-11 22:18
1993 年,百花书局诞生于苏州;三十余年来,它始终与昆曲文化深度捆绑。在接到百花书局改造的任务时,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尺度极小、年久失修的附属用房。它原为中国昆曲博物馆内部的一间书屋,面积仅 65 平方米,常年作为博物馆出口,功能与结构已基本脱离原有文脉。但我们并未仅将它视为“空间改造”,而希望它能重新纳入博物馆的文化系统中,成为一个具有“生产能力”的“书店 ”模式新节点。


01
“堂名担”:传统戏台的便携性逻辑


我们从一个极小的元素切入:一件常被忽略的博物馆藏品 —— “堂名担”。这是我们介入设计的起点,也是整个空间改造的主轴。
“堂名担”是江南传统戏班中使用的便携式门面结构。结构轻巧、可拆可合,是一种“走着演”的舞台机制。这类构件虽然微小,却浓缩了古代戏曲文化的移动性、适应性与组织结构,也体现出舞台精神与民间社会之间紧密的互动关系。我们不复刻它,而是提取其中的逻辑,并转译为当代表达的空间语言。


堂名担 © 青天制作所


堂名担 © 青天制作所
02
一种“可被带走”的剧场意识
百花书局的空间改造,围绕“堂名担”展开。它不再是单一功能的展陈场所,而是被重新定位为一个动态的文化发生地 —— 一个“嵌入式的微型剧场”。我们把“堂名担”从昆曲语境中解构为三种空间元素:标识性、生成性、可移动性,并据此建立起书局的空间策略。


初步概念设想 © 青天制作所


© Wen Studio


© Wen Studio
整个空间的视觉与动线中心被交由一个独立装置承担,它即是“新堂名担”。不是道具,也非纯装置,它游走于“剧场门面”与“构造核心”之间。在这个不到 7 平米的结构中,我们置入了四面不同材质与语意的立面,使其在物理上定义空间中心,在象征上激活仪式感,在操作上支持不同活动的灵活展开。


轴测图 © 青天制作所


© Wen Studio


© Wen Studio
03
拆与合:从演出逻辑生成空间逻辑
我们没有追求空间形式上的“像舞台”,而是更专注于舞台如何生成。传统戏班带着“堂名担”走街串巷,其空间逻辑是拆—合、开—聚、现—隐。这种方式启发我们建立起空间的基础机制:所有展陈结构都可移动;墙面为磁吸系统;帘幕可收合;导视为模块化 —— 这是为了让空间可以轻装上阵、快速转场,支持多样的文化活动从日常中生成。


新“堂名担”的所有零件 © 青天制作所


© Wen Studio


© Wen Studio
例如北侧墙面设有三组带轮装置的木展墙,既可贴墙展陈,也可推动至中央围合空间,与“堂名担”协同形成临时剧场。西侧为戏曲黑胶展区,借由“堂名担”西面可开启门板与镂空窗,观者可透视另一空间中的播放装置,强化“台前台后”的视觉联系,形成文化事件可预见、可延展的临界状态。


© Wen Studio


© Wen Studio


© Wen Studio


© Wen Studio
04
材料转译:从旧门板到穿孔钢板
“堂名担”的北面使用了现场回收的旧木门板,我们以炭烧工艺将其脱漆显纹,使其转化为温润的木肌底色。镂空的花窗被保留,作为来自前身空间的“文化残件”,它不是背景,而是成为新的叙事接口。


© Wen Studio


© Wen Studio


© Wen Studio


花窗语言 © 青天制作所
南面则反向使用当代语言。我们以工业材料 —— 穿孔镀锌钢板构成其立面,打孔图案脱胎于昆曲演员头面上的“一弯”结构,通过抽象提炼与图案重组,形成一种“像传统又不是传统”的模糊秩序。细看每一块钢板,它的几何节奏实则源自“堂名”书法的线性笔触。


© Wen Studio


© Wen Studio
05
以叙事书写空间构造
此次 65 平米的小空间里,我们希望并非强调“设计完成”,而是像传统的“堂名担”,强调其可再书写性:空间可以被反复使用、被不同使用者接管、被新叙事重新嵌入。
百花书局定格动画 © 青天制作所
近两年我们持续尝试在一些尺度较小、处于边缘状态的城市公共空间中,探索“最小介入”下的结构再生与文化嵌入。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条件受限、预算有限、公共性模糊,设计无法依赖单一形式的表达,也难以通过一次性完成来实现“项目闭合”。但正是在这些缝隙空间中,我们反而找到了可能:通过一种轻量、嵌入式、可再书写的空间结构,使它们重新被公众看见、使用,并参与到新的叙事当中。


© Wen Studio


© Wen Studio


平面图 © 青天制作所


剖面图 © 青天制作所


剖面图 © 青天制作所


花窗语言的再探索 © 青天制作所
建筑事务所:青天制作所
项目地址:苏州,中国
项目年份:2025 年
项目面积:65 平方米
主创设计:包理佳 Freja Bao
设计团队:刘姝岑、杨祖铭、朱弘轩、冯羽优(实习)、杨佳怡(实习)
模型及视频拍摄:青天制作所/朱宏基(实习)
视频及音频制作:青天制作所/高欢悦、刘姝岑
施工:上海中耕装饰
灯光:辰弈设计 WIN Design Consultant
业主:情调苏州,中国昆曲博物馆
空间摄影:Wen Studio
编辑 Yulin
排版
Yu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