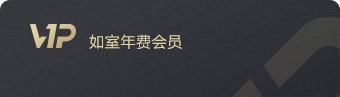Interview: Renzo Piano on The Shard | Dezeen
2012-05-18 16:20
随着碎片在伦敦接近完工,这是在300米高的塔楼开始工作之前,建筑师伦佐·皮亚诺接受采访的记录。
在Dezeen主编马库斯·费尔斯(Marcus Fair)的采访中,皮亚诺勾画了这座后来将成为西欧最高塔的大楼,解释了设计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如何得到昵称的,以及为什么作为一名建筑师,他总是避免拥有一种可识别的建筑风格:
伦佐·皮亚诺:是[阿尔普结构工程师]托尼·菲茨帕特里克打电话来的,他说,你想见见什么人吗?有人是[开发商]欧文·塞勒[塞勒地产集团]。我们在柏林认识的。我被…的想法吸引住了不是建造一座高楼,而是建造一座混合用途的高塔--一个垂直城市。
上图:建筑渲染工作室AVR伦敦对碎片的可视化,出版于2009。
很明显,这座塔坐落在一个由不同交通工具组成的交叉系统的中心--火车、公共汽车等等。因此,这是我们过去在布朗菲尔德所做的典型工作--如何加强城市的生活。这种哲学以爆炸和开始内爆来超越城市的扩张。城内成长:填洞,填工业用地,铁路用地。然后我们开始工作。
所以这是个开始。为什么我们想出这个(碎片的形式)是有点困难。吸引我们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混合使用的想法,以及它坐在一个重要的交换场所。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展示你可以在不增加交通流量的情况下在城市里生活--通过公共交通。
我第一次在伦敦(当时的伦敦市长)见到肯·利文斯通(KenLivingstone)时,很明显肯对此感到高兴。这完全符合他的哲学。最后,我们的哲学,客户的哲学,肯的哲学,以及城市的哲学终于走到了一起。这是相当幸运的。
接下来的事情是,如果你必须将办公空间、酒店空间和住宅空间组合起来,你很快就会明白,对于办公室来说,你需要那个大平台(用手示意),对于你需要那么大的酒店,对于你需要那么大的房子,你很快就会明白。所以,如果你需要那个和那个,你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形状?
在某些方面,很难在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理性和本能之间--进行澄清,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发胖和变小的想法是一个理性和本能的过程。理性,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有意义。本能地,因为很明显,要使事物变得优雅,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填满天空--使一些东西变得苗条。
不,它也是通过素描和模型制作而来的。伊尔文第一次来办公室时,我开了个玩笑;我在车间里捡到一块碎片--不是玻璃碎片,而是木头碎片。一块碎片。我开了个玩笑。其实是很直接的。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即使是在柏林--这可能是欧文·塞勒神话的一部分--他上次提醒我,午餐时我拿起一支铅笔,开始画草图。我们从一开始就谈论得相当广泛,然后越来越少(Piano在一张纸上勾勒出建筑的草图,下面),我们的想法是做一些可能正在打破规模的事情,在这个位置上出现,在这里有一个观察甲板,当然这里有一个公共空间,从这里到这里的住房,从这里到这里的酒店,这里的办公场所(…)。这东西来得很快。
是啊,差不多吧。但我不想制造神话。当然,从第一张草图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这个高度(表示建筑物的上层),你有相当多的风,当你下降到低于50平方米(每层)时,你将无法使用这个空间,所以我们开始想出散热器的概念[这是一种在建筑物上方的翅片式传热装置。“”。。。在早期的迭代中,但后来被一系列的公众观看画廊所取代]。
如你所知,我们的目标是节省大量能源。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悉尼所做的;五、六年前完工的奥罗拉广场塔,实际上节省了那里前一栋建筑的三分之一的能源。在那里,我们在冬天的花园里使用微风,在玻璃中使用化学物质。玻璃技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正在做不同的事情。一是因为这是一种混合使用,我们有额外的生产热量,从办公室,我们可以再利用在住宅部分。这是不诗意的,但很聪明。
另一件事是玻璃的组成。我们使用的是双层玻璃--实际上是三层玻璃--在我们有薄片的地方--威尼斯百叶窗--可以减少太阳的热量。当你没有阳光时--这发生在伦敦--你就可以把层板抬起来。他们在玻璃里。当然,两块玻璃之间的空气会升温,但我们会把它疏散,然后再利用它。
所以,外观的构成是神秘的一部分,也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们正在研制一种化学玻璃,其成分为…。百叶窗比彩色玻璃好。你可以看到他们。到了晚上,它们就会消失。会有一些方面,可能甚至不会有层板。它就像一棵树的树干,它的运转方式各不相同,取决于它得到多少太阳。南面和北面不一样。
我们不使用镜子玻璃或有色玻璃。我们使用更微妙的新技术。建筑的语言将取决于此。我们将使用透明玻璃-低铁玻璃。在英国,它也被称为超白玻璃。这与普通的玻璃非常不同,它是非常绿色的。如果你使用低铁玻璃,你会得到一些真正像水晶的东西。因此,取决于白天、光线和太阳的位置,建筑看起来会有所不同。它不会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玻璃陨石-乔姆!就像许多塔一样。它会变得更加充满活力和变化。
上图:摄影师尼克·伍德和建筑渲染工作室海斯·戴维森(HayesDavidson)的视觉化,这是去年在Dezeen上出版的系列作品之一。
你如何确保这样一座高楼大厦能够赞美它所在的城市,而不是破坏它呢?
这是个好问题。塔通常有一个非常坏的声誉-通常是一个应得的声誉,因为它们通常是傲慢和权力的象征。换句话说,故事塔通常讲的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微妙。它们只是关乎权力和金钱,但建造一座塔的想法并不仅仅是一个糟糕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上升的欲望并不是真的要打破任何记录--它是呼吸新鲜空气。它是去享受气氛。所以我认为关于宁静的第一点是,建筑并不是在挣扎着变得强大。其实挺温和的。尤其是从街道上看,建筑物不是那样,而是那样,因此它会反射天空。
这一切都是为了建造一座不傲慢的建筑。我不认为傲慢会成为这栋建筑的特征。我认为它的存在将是相当微妙的。尖锐但微妙。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失去存在和强度。我想这幢楼会很紧张--不胆小。
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你说:“我们必须有信心,相信我们可以建造一座伦敦人尊重的塔,因为他们尊重圣保罗。马蒙的力量创造了一座像西耶纳一样美丽的城市;这种力量可以被用于良好的公民用途,而不仅仅是为了让开发商富有。“你相信吗?
我经历了很多次这个练习,包括在RIBA的一个会议上,当时每个人都在谈论在伦敦增加塔楼。我说过我不认为伦敦是一座高塔之城。我认为曼哈顿是一座由塔组成的城市,在那里是有道理的。我不认为伦敦是一个由塔楼组成的城市,我也不认为加强城市生活的唯一方法就是建造塔楼。我不认为通过内爆(而不是周边地区的爆炸)实现增长,必然意味着建造塔楼。伦敦金融城,那里的建筑物通常是两到三层楼,你可以很容易地增加城市的密度,而无需建造塔楼。
在伦敦,我看不到很多地方可以造塔。另外,如果你建了一座塔,你就投下了阴影。有趣的是,我们的影子投在河上。我们不投影子…
你坐在一个伟大的交通枢纽之上。有很多东西使得这座建筑在那里成为可能,而不是在其他地方。我认为这是少数几个你可以有塔的位置之一。
首先,马库斯,它只会是几个星期内最高的!我开玩笑呢。它不是最高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使它成为最高的。当你停在这里的时候,它不是最高的。我们没有试图打破任何记录。
但我认为你正在触及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关于风格的讨论,格罗夫,可识别的手势。我相信这是建筑明星体系的一部分,但对于建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故事,因为它不是赞美建筑,而是赞美建筑师。我认为最终对建筑不好,因为它最终限制了自由。作为一个建筑师,让我们假设你有一定的成功,你总是被逼着重复自己。这不仅适用于建筑师,也适用于画家、作家、电影制作人。如果你做了什么,人们会要求你再做一次。但这不是一个好故事,这是缺乏自由。
每个人都在谈论缺乏自由,但最难保持的自由可能不是来自别人,而是来自你自己。摆脱他人的自由是很容易的;如果你有一群坚强的人像我们一样一起工作--老实说,我们很好地捍卫我们的自由--但最危险的捍卫自由的是和你自己在一起的自由。因为你习惯了,你就变得自我参照,因为事情进展顺利。所以你掉进了大陷阱,这是一个可识别的标志。你这样做事的想法。所以人们马上就会说那是皮埃尔·卡丁,赫尔墨斯什么的。我并不是说这是一个道德家;我讨厌重复的姿态或自我参照的态度;我讨厌被需要提升你的格里夫--你的标签--困住的想法,但同时我也喜欢连贯性的想法。我喜欢建筑师有自己的语言的想法。我们必须不断抵抗自我重复的诱惑。
上图:建筑摄影师保罗·雷特利和导演丹·洛的时间流逝电影,展示了碎片建造的最后阶段,本周早些时候在Dezeen上发表。
建筑不是建筑。建筑是艺术,但艺术却被许多其他东西严重污染。从最好的意义上讲,它被许多东西污染了。但我开始认为建筑就是艺术,从建筑开始。
这很好,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让我远离学术界。当你年轻的建筑师,你总是有陷入学术陷阱的危险。学术界是在不了解冰山底部的情况下做出形状的态度。但是如果你变得更谦卑——62和63,我在米兰大学睡得比在床上多。这是真的,我来自一个建筑家,但我也来自一个非常强大的社区生活的社会经验。和其他人一起生活,改变世界,睡在大学血腥长凳上。所以这个滑稽的混合,这个有趣的BoababaSeSE的情感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说来自建筑商的家庭本身就是一件好事,这是很愚蠢的,因为你以后可以学到,但是它是好的,因为它让我远离了礼节。来自学术界,来自于创造形式的轻松愉悦。
学术界不仅在建筑领域,而且在写作、绘画、音乐方面--所有这些都是没有反抗的。当你年轻的时候,这是非常危险的。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学生的时候,意大利的教育体系是高度学术性的。就像在法国一样。法国现在不同了,但别忘了艺术学院已经宠坏建筑师多年了。创造假艺术建筑师。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建筑家族出身让我远离了这一切。它让我远离太容易陷入手势的乐趣。
乔治·庞皮杜中心(TheCentreGeorgePompidou)(建筑钢琴在1971与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Rogers)的比赛中获胜,开启了两人的职业生涯,并以服务管道和外部管道而闻名)对你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风格上的陷阱。
首先,人们认为你会把你的一生都花在制作管道上!
他们要求你制造管道。
艺术家也是如此。
例如,如果你像贾科梅蒂这样的伟大艺术家。
Giacometti花了过去10年的时间重复同样的事情——因为他被要求重复同样的事情。
那个可怜的家伙——他很好,很温柔。
这并不恶心——他不是为了赚钱还是做什么,只是一个陷阱,他掉进了圈套。
从定义上说,建筑是一门学科--当然它是一门艺术学科,它是一门科学、社会学科--但它是一门充满冒险精神的学科,因为每一项工作都是一种新的冒险。这与在伯尔尼建造保罗·克莱恩博物馆完全不同。完全不同。你怎么能用同一种语言讲述如此不同的故事呢?你怎么能担心这个?但是如果你有内在的一致性,你就不用担心了。反正这个会来的。但如果你开始担心,你就会掉进陷阱。你担心的不是自由,而是“人们将如何认识到这是我的”,这并不重要。
马库斯,我不在乎,但人们总是告诉我他们认识它。有个人去看了我们的一栋楼,但他不知道那是我们的。如果有什么是相干的…如果你问我这件事的痕迹是什么,我想比以往更多的是用同样的材料,总是同样的节奏,它更多的是一种对轻盈的渴望--例如,对透明度和振动的渴望。
这与我们对“纽约时报”的尝试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纽约时报”在纽约建造了一座陶瓷幕墙。这背后的诗意是相似的--它是关于振动,成为大气的一部分,蜕变。轻盈,透明,也许是建筑和建筑之间的紧张。
有一定的特点。我不认为我应该担心它,但一些评论家告诉我们,他们通常谈论这个-一个空间也是由无形而建立的情感。这不是我的想法-[建筑评论家]雷纳巴纳姆讨论了良好的环境。建筑有时是由非物质性建立起来的:光、透明度、长视角、振动、颜色、张力。我宁愿在这个采石场挖洞,也不愿重复某些姿势。
听着,我很幸运,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建筑师时,我在米兰接受了教育,去探索城市,把我的手投入科学,乌托邦,去改变世界。这就是你年轻时所做的事-叛逆。别忘了,当你年轻的时候,叛逆是找到自己最便宜的方式。然而,当你60岁的时候,你怎么能接受拥有一种风格的耻辱呢?被商业义务抢走。这是一种羞辱,这是侮辱。作为一名建筑师,这就是你必须追求的目标。这种自由--也许你永远不会改变世界,但你必须相信你能做到,否则你就迷失了。
所以每次你得到一份新工作,你的方式就是说啊…但是,你怎么能说不,不,不,忘了这一点来羞辱自己呢?首先,我们如何才能让自己被认出来。
如果有人来问你“我想要一栋外面有管道的大楼”,你会怎么说?
我会笑。你知道在你的生活中有那么一刻人们不再来说那些愚蠢的事情。我们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能够决定做什么。
但是像这样的挑战在城市的历史中有着很深的根源,在科学史上,所以这里有一种乌托邦。这不仅仅是一种正式的姿态。即使是一个垂直城市的小概念,混合使用,加强生活,而不增加新车。你知道我们在这栋楼里有47辆车[碎片]。这个停车场有47辆车.不是4,000。这也是因为肯·利文斯通也说过不要添加…只是为了残疾人和诸如此类的用途。
所以这里有很多东西是建筑中看不见的部分。有点像冰山。看不见的部分是我所说的城市的社会愿景,环境和诸如此类的东西。那里很坚固。除非你这样做,否则架构很快就会变成一种学术练习;一种正式的练习。
许多人声称乔治中心蓬皮杜中心是第一幢“高科技”风格的建筑。那是一次正式的演习吗?
事实上,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建筑。它不是真正的宇宙飞船——它是Jules Verne宇宙飞船。这实际上是对技术的模仿,而不是对技术的模仿。这只是一种直接和非常天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通常在60年代和70年代之间的恐怖文化机构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在这个城市[巴黎,在他的工作室是基于] -和现代建筑,非常开放和一个奇怪的关系与人。想法是它不会吓唬人。我们是年轻的坏男孩,我们喜欢这样。
但波波并不是科技的胜利。更多的是关于生活的乐趣。这是一场叛乱。
“碎片号”即将在伦敦完工,这是建筑师伦佐·皮亚诺在300米高的塔楼开始施工前接受建筑师伦佐·皮亚诺采访的记录。在德泽恩主编马库斯·费尔斯的采访中,皮亚诺勾画了这座后来将成为西欧最高塔的大楼(上图),并解释了该设计是如何进行的。
 举报
举报
别默默的看了,快登录帮我评论一下吧!:)
注册
登录
更多评论
相关文章
-

描边风设计中,最容易犯的8种问题分析
2018年走过了四分之一,LOGO设计趋势也清晰了LOGO设计
-

描边风设计中,最容易犯的8种问题分析
2018年走过了四分之一,LOGO设计趋势也清晰了LOGO设计
-

描边风设计中,最容易犯的8种问题分析
2018年走过了四分之一,LOGO设计趋势也清晰了LOGO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