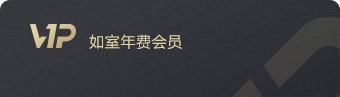Alexandra Lange on the Portland Building and Postmodernism
2014-11-06 19:10
观点:有时候,拯救一座似乎不起作用的建筑物变得很重要。亚历山大·兰格说,迈克尔·格雷夫斯的后现代主义典范波特兰大厦就是这样。
在新展览的第一堵年表中心,迈克尔·格雷夫斯:过去作为序幕是一个小小的架子。架子上有一个装饰得像他的波特兰大厦(1982)的饼干罐。这个比例似乎有点不一样,因为锡比它宽。在我看来,波特兰大厦是一个完美的立方体,更接近它从人行道上缩窄的外观,更接近于我第一次介绍格雷夫斯作品的彩色正面画。
在我的记忆中,这些立面图都是方形的,由三角形和半圆、矮胖的柱子和方形的窗户组成,很适合将其转换成动画设计的GIF作为二维构图的练习。1985年,当格雷福斯来到惠特尼博物馆时,他试图让马歇·布劳耶的正面变成其中的一块,顽固地卡在他的左下角。但布鲁尔的建筑抵抗饼干罐。它可能会翻倒。在书架上看起来很乏味。格雷夫斯建议比斯科蒂时,布鲁尔似乎不太可爱。
这场展览庆祝了格雷夫斯50周年的实践,时间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格雷夫斯(Graves)--以及他仍然是海报男孩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又重新出现在新闻中。波特兰大厦现在需要9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95万元)的升级费,这让人们开始更多地谈论它的价值。当格雷夫斯本月早些时候在波特兰发表讲话时,他对这个城市可能会拆掉它的想法感到痛苦,这是不出所料的。对他来说,“这是如此的闪亮,它是如此的令人振奋。那是波特兰迪亚,那是大楼。“
但那是外在的。当被问及那些小色彩的窗户,低天花板的高度,建筑物后面公共绿地上的巨大停车位时,Graves通过Buck回到城市,指责客户为车库,窗户的能源危机,天花板的预算。听起来像是一种任性的表演:“你为什么不爱我?”我的房子里所有这些地方你都讨厌吗?不是我的错。事实上,建筑的所有部分都是在饼干罐头上没有显示的部分:内部,背面,潮湿的侧面“Logias”。“Graves似乎敢于批评一些城市的预算——把他的建筑看作是一个空的装饰性的外壳,它总是被指责为。(这是一个两星期的建筑琐事。)
自从我2013第一次访问波特兰大厦以来,我一直在为自己对波特兰大厦的感受而挣扎。在那次访问之后,我写道:“它已经不太老了。更准确地说,它看上去像屎。肮脏,潮湿,带着一条阴暗的深邃的拱廊。这种颜色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酒店舞厅出现的。它积极地填满了整个街区,几乎没有空间来审视其集中的成分。“
那太粗鲁了,但这就是我的感受。格雷夫斯认为他的办公楼是像波特兰或路易斯维尔这样的旧砖石建筑和铸铁建筑之间的人文阶梯,然后是新的直立玻璃塔。我发现他的瓷砖比现代主义的邻居更为疏远,其中包括Pietro Belluschi早期的、极其高雅的公正大厦和Lawrence Halprin崎岖的开阔空间。如果建筑对内部员工不好,对外面的城市不好,那有什么意义呢?
当你主张拯救一个野蛮主义建筑的保护者目前的困难儿童,比后现代主义年龄大十岁时,你必须把谈话转移到对意图和发明有帮助的外表上。格雷夫斯似乎在试图推翻这一策略,以图解的方式定义人文主义。波特兰建筑的重点,是它自己的建筑师关心的部分,是它装饰的表面。今年早些时候,Karrie Jacobs在为波特兰建筑的奇异性辩护时写道,她曾与前俄勒冈州建筑评论家Randy Gragg交谈过。
“它是否像站在那里一样,通过照片影响它?”这真的是你必须经历的东西,才能理解它的重要性吗?我想,也许不是。“
走过墓碑回顾展,饼干罐并不是唯一值得注意的桌面项目。他为Alessi提供的1984-85银制茶服务,这是一款全新的产品,是一套漂亮的,甚至强大的物品。阿莱西不锈钢茶壶,仍然伟大;目标版本,不错。我们确实有格雷夫斯,感谢精简和照亮了大量的日常家庭产品。
我喜欢为金伯利设计的新手杖--克拉克--从2003开始腰部以下瘫痪,格雷夫斯将他的部分实践投入到医疗设备和设施的必要重新设计上。在兵马俑,提尔和茄子,他们有不同的疾病形状的手柄,和基础设计,使拐杖在踩上的时候出现。
在那个比例上,颜色感觉很吸引人,不便宜;形状不是任意的,而是适合手的。在城市规模,手在哪里(或什么)?这里的操作短语是“在那个规模”,因为这一直是格雷夫斯的架构的问题。它可以看起来像一幅画或一个锡,但当你的茶具和你的建筑模型有相同的形状和组成节奏,其中一个现实将失败。(当你看到建筑明显受到格雷夫斯的影响时,就像立方体中的FAT社区一样,人们只能希望它超越小屋内的空茶壶和超图形的后面。)
其结果是波特兰大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地方,我们作为批评者,必须捍卫它的表面价值--但我相信,只是因为它的脸。我不能为它制造太多的情绪,但在这种颠倒的情况下,这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指标。后现代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风格了,但是我们真的很乐意摧毁它最突出的典范吗?当我想到那些我会拆除的建筑时,它们往往是二流的:已故的戈思美,在阿斯托的地方,或者在耶鲁。雅各布斯说得对:“当你的判断被鄙视蒙蔽时,做一些不可逆转的事情是个坏主意。”这就是布鲁塔主义的拥护者一直在说的关于混凝土的话。
迈克尔·库博(Michael Kubo)、马克·帕斯尼克(Mark Pasnik)和克里斯·格里姆利(Chris Grimley)在他们的“维护布鲁塔里主义”(Defense Of Brutalism)一书中写道,对这种风格的批评往往与建造它们的城市重建计划有着同样的关系,所以,也许,格雷夫斯的波特兰大厦,加上一个肠道内部装修,为了更好的措施,可以。我讨厌告诉一个城市,它必须保留我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但历史确实改变了人们的看法。通过定义什么是值得保留的象征,几乎像饼干罐的墙壁一样薄,有机会使它成为一座建筑,可以作为建筑,而不仅仅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二维图像。
亚历山德拉兰格是一位纽约的建筑和设计评论家。她是哈佛大学2013-2014学年设计研究生院的勒布研究员,著有“建筑写作:掌握建筑和城市的语言”以及电子书“点城:硅谷城市主义”(The Dot-Com City:硅谷Urbanism)。
迈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PastasPrologue)将于11月22日在纽约新设计学院帕森斯(Parsons)举办,这是一场与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史蒂文·霍尔(Steven Holl)和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等演讲人
阅读更多建筑后现代主义迈克尔格雷夫斯意见亚历山德拉兰格
有时拯救一座似乎不起作用的建筑物变得很重要,比如迈克尔·格雷夫斯的后现代主义波特兰大厦,亚历山德拉·兰格说。
 举报
举报
别默默的看了,快登录帮我评论一下吧!:)
注册
登录
更多评论
相关文章
-

描边风设计中,最容易犯的8种问题分析
2018年走过了四分之一,LOGO设计趋势也清晰了LOGO设计
-

描边风设计中,最容易犯的8种问题分析
2018年走过了四分之一,LOGO设计趋势也清晰了LOGO设计
-

描边风设计中,最容易犯的8种问题分析
2018年走过了四分之一,LOGO设计趋势也清晰了LOGO设计